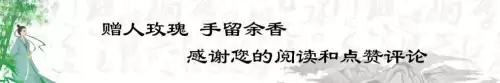【崆峒书生读西游|第026回】
导语与现实世界相比,《西游记》描述了一个奇妙的幻想世界,但要肯定的是,这个世界是立体的、多角度的、有延续行性的,从空间角度看,仿佛是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拓展;从时间角度看,仿佛对岁月轴线的扩充。更重要的是,这个虚幻的世界里,有佛法,有仙道;有善良,有邪恶;有人民,有国王;有因果,有循环,这里既有世间的人与物,还有世间没有的神和仙。
与其他文学作品不同,《西游记》通过世间真实的人性、物性,融汇以虚幻的神性,以取经为线索,以佛法为引子,展示给读者一个奇幻绚丽的美妙世界,留给后世一座真与幻的艺术宝库。
人性:《西游记》万千人物形象的基础人性是《西游记》中所有人物形象的基础。按惩恶扬善的佛法指向,《西游记》中的人物按角色形象基本可以归为两派,一派是善良,以仙佛为代表,一派是邪恶,以妖怪为代表。
在善与恶的中间,仙佛共同开辟了一条惩恶扬善的道路,这条路就是通往西天的取经之路,整个作品也是基于这样的结构展开描述。
仙佛世界的人性与对真实生活的折射相同,《西游记》秉承“邪不压正”的理念,给善良给予了强大的力量,这些力量基本围绕仙佛为核心展开。仙佛虽然是虚幻的存在,但他们身上体现的人性却是从万千人类角度出发的真实凝结。
比如《西游记》中以如来为首的佛门力量,就不再是生活中那冷冰冰的石佛模样,或许现实生活中如来的言谈举止只能靠人们的臆想去领会,但《西游记》中的如来却是一个有血有肉的“人”的样子;再比如观音菩萨,经过漫长的形象演变历程,她以一个面貌较好、身形丰韵、心性善良的女性形象在《西游记》中出现,这样的形象更具“人情味”,比如在收服鲫鱼精时,孙悟空见观音没换衣服,还提醒她“着衣登座”后再去降妖,再比如为了劝孙悟空跟随唐僧西去而给他三根救命毫毛时,观音菩萨更像一位温和而又用心良苦的“慈母”。

除了如来与观音为代表的佛门,仙道居住的天庭生活也展示给我们人性的一面,比如玉帝,他俨然成为天界的最高掌权者,但这个掌权者是以一个“人”的形象存在,他会生气、会计较,还会发怒;再比如托塔李天王,按照《西游记》中第83回中的讲述,他虽为天王却和人间一样,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,还有一个干女儿(老鼠精)。
取经团队的人性作为故事的主角,以孙悟空为首的取经团队身上更具浓浓的人性。
比如孙悟空,作为智慧与执行力的浓缩,遇事容易着急、毛躁,但又有勤奋肯干的一面;
比如猪八戒,简直是生活中那些好吃懒做、不思进取的人物自画像;
比如唐僧,活脱脱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愁善感的“玻璃心”;
比如沙和尚,虽然在取经路上的分工往往以看行李守师父为主,但他身上浓浓的老好人味道,依然是我们生活中真实人性的折射。

与仙佛与取经人一样,妖魔鬼怪虽然代表邪恶,但他们身上依然有着丰富的人性。比如九头狮子精,当自己的狮孙们被孙悟空打死时,他会心生愤怒然后引兵报复;比如蝎子精,她一心只想与唐僧成亲,结成美好姻缘;再比如豹子精,当拿到唐僧以后,他悠然做起美梦,但愿吃一口唐僧肉能长生不老,殊不知,与他的美梦相对应的是,以秦皇汉武为代表的人类,也曾做过长生不老的美梦。
人性是打通《西游记》这样一部文学作品与读者共鸣的第一性,如果没有人性,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将变的僵化生硬。而在人性的基础上,《西游记》又对世间万物进行融合与加工,让真实的人性轻巧自如地驾驭在万物之上,这是《西游记》艺术魅力的第一次飞跃。
物性:《西游记》真幻艺术魅力的中坚《西游记》中的物丰富而繁杂,无论是土生土长的植物,伏山住洞的动物,还是空灵漂浮的云朵,作者都能轻巧自如的整合使用,使其与对应的人物形象凝聚升华。
《西游记》中植物成精的比较少,但在仅有的几个植物妖精当中,与其对应的物性依然是这些妖怪的植物特性。
比如《西游记》第六十四回中“木仙庵谈诗”一节,通过“松、柏、桧、竹”四种植物的物性挖掘,体现出了不同风格与特性,这一物性便通过他们的诗作直接传达给我们。
以松树为化身的孤直公作诗曰:
我岁今经千岁古,撑天叶茂四时春。香枝郁郁龙蛇状,碎影重重霜雪身。
以柏树为化身的凌空子作诗曰:
吾年千载傲风霜,高干灵枝力自刚。夜静有声如雨滴,秋晴荫影似云张。
以桧树为化身的佛云叟作诗曰:
岁寒虚度有千秋,老景潇然清更幽。不杂嚣尘终冷淡,饱经霜雪自风流。
以竹子为化身的十八公作诗曰:
我亦千年约有余,苍然贞秀自如如。堪怜雨露生成力,借得乾坤造化机。
对比四种树木的诗句风格,很容易感受到诗句中与其对应的物性,再看他们的名称与谈笑风生,无疑又是一次人性化的升华。

在谈论诗歌正热闹时,杏仙出场了,通过其与唐僧的不羁风流言谈,杏仙与杏花对应的轻佻物性表现的更为淋漓尽致。
与稀少的植物成精相比,动物妖精在《西游记》中是最常见的邪恶类别,而每一个动物妖精的身上,都有对应的物性体现。
比如唐僧去盘丝洞化缘时遇到七只蜘蛛精,这些蜘蛛精通过肚脐眼吐丝的形式,把唐僧以仙人指路的造型俘获在洞中,这里的丝正应了蜘蛛能吐丝的天然物性;比如蝎子精在掳走唐僧以后,孙悟空与猪八戒上前叫阵,随后二人与蝎子精开始打斗,“那女怪将身一纵,使出个倒马毒桩”,孙悟空的头皮被扎了,疼痛难忍,这“倒马毒桩”正是利用蝎子会蜇人的天性。

除了以上动物,观音池中的鲫鱼精一下界就霸占了通天河,以水府为居,这是鱼离不开水的物性;文殊、普贤二位菩萨的青狮、大象精一下界就占据了狮驼岭为王,这是兽居深山的物性。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,险山恶水中频繁出现妖精,黑熊怪、黄风怪、犀牛精等等,无一不是如此,无一不是生性与幻化妖魔的结合。
除了动植物,《西游记》中还有一些独特的物性描绘,这些描绘无疑成为锦上添花之笔。
孙悟空一个跟斗能翻十万八千里,菩提老祖给他一个轻盈美丽的筋斗云,与“轻盈”“飞翔”“快捷”的物性相比,筋斗云无疑成为孙悟空的点缀式加成。而除了这种小点缀,《西游记》的大环境构成,才是最为壮观的。
前文提过《西游记》中的环境是人间生活场景的拓展与延伸,在“李世民游阴”一节中,作者通过“恶鬼”“冤魂”的特性描绘出了一个阴森恐怖的幽冥地府;按照仙道的轻盈自修,又把天庭的府邸放在云端;按照龙王与龙兵虾将的特点,又有东南西北四海龙宫,同时还有各地井龙王与河龙王。这些都是结合具体物性的延伸与设定。
《西游记》中的三界地域广阔,上到云端,下至深海,东到大唐,西至灵山,此间万物都按照特有的物性进行设定,他们的有序铺设是每个角色形象展现人性的核心场景,更是人性化的万物展现神性飞跃的中坚地带。
神性:《西游记》幻想艺术魅力的升华如果仅凭人性和物性的结合,《西游记》的艺术魅力一定会受限,与之齐名的《三国演义》中的史诗大场景、《水浒传》中的豪迈兄弟情、《红楼梦》中的细腻闺阁事都会在艺术层面超越它,如此说来,神性的植入无疑是《西游记》艺术魅力更上一层楼的制胜法宝。
与朴实无华的人性与不可脱离的物性相比,神性则缥缈虚无、不可琢磨,在志怪小说的领域里,有由于过度神化而被剔除的,也有神性不足而被埋没的。而大胆自如的使用神化手法,是《西游记》中植入神性的一大准则。
比如故事之初的孙悟空,简直成了无敌的存在,可大可小的金箍棒,长生不老的仙丹,延年益寿的御酒与蟠桃,这些物体的大胆神化让孙悟空成为超越一切的存在,玉帝屡屡征讨无果又让孙悟空日益骄横,如果没有故事后续,此时孙悟空身上的神性已经泛滥,作品也濒临过度神化的边缘。但太上老君的金刚琢与如来佛祖的五指山,又合情合理、收放自如的把故事从过度神化的边缘拨回正轨,在“五行山下定猿心”后,再度阅读时读者依然觉得顺理成章。

大胆的使用神化,还体现在对法宝属性的大胆赋值。金兜山金兜洞里的兕怪(青牛精),凭借手中的金刚琢不仅“没收”了孙悟空的金箍棒,还把众仙的武器通通收走,就连如来派来的十八罗汉放出的金砂都被收走,一时间,凭借一只虚无缥缈的金刚琢,青牛精很快成为天地间不可俘获的妖怪。虽然青牛精最终被老君收走,但通过这样一件法器的大胆神化,《西游记》却为我们展现出神化手法的催化之下不凡的艺术效果。
如果以上都是大胆的使用神性,那唐僧的出生与家事变故却是神化自如的表现。唐僧父亲陈光蕊进京赶考、街头招亲、江州赴任、遭遇厄难,以及后来殷温娇产子抛江,这一系列故事几乎就是平铺直叙的罗列,也是《西游记》这样一部神话小说中不多见的白描手法。但随后通过龙王还魂的神化反转,让整个故事瞬间复活,正义最终战胜邪恶,而鲤鱼报恩的前因后果又让整个故事情节合理,逻辑严谨。
在大胆与收放自如的使用神化之外,《西游记》中的神性也为读者带来了无数乐趣,鲁迅先生之所以称之为“游戏之作”,除诙谐幽默的文笔外,还有对神性的幽默加工。
比如“黑风山怪窃袈裟”一节中,那贪得无厌的老方丈对袈裟动心以后,听从弟子的恶毒意见纵其放火烧禅堂,面对燃烧的熊熊大火,孙悟空没有唤醒师父,而是找广目天王借避火罩罩住唐僧,在神性的基础上无疑多了一份诙谐,让恶人自食恶果。

再比如金、银角大王那一节,当银角大王派精细鬼伶俐虫拿红葫芦与净瓶去收孙悟空时,孙悟空拔一根毫毛变一个大葫芦并声称他的葫芦能装天,更让人捧腹的是,他还上天找玉帝,在哪吒的建议下,还真找真武借了皂雕旗“把那日月星辰闭了”,上演了一回“装天把戏”,成功骗走了红葫芦与净瓶。让人捧腹的幽默之处在于,纵然让人肃然起敬的玉帝,也会玩性大发,纵使孙悟空玩把戏,不仅不制止反而纵容相助。
结语《西游记》是神话小说的巅峰之作,这部凝结了历史、神话与传说的作品,通过光怪陆离的三界环境和降妖除魔的取经正道,把佛道仙境、人间山水、妖魔洞府熔于一炉,又通过人性、物性和神性的完美结合,绽放了幻想的独特艺术魅力。
纵观《西游记》,人性通过物性展现,神性在此基础上完成飞跃,却又回头反作用于人性与物性,三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相作用圈,共同作用、缺一不可。
《西游记》的神话艺术是虚无的艺术,更是幻想的艺术,基于“玄奘取经”这样一则史实,从东土大唐出发,作者展开了想象的翅膀,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西翱翔,正是这双想象的翅膀,让这一路上的自然之物有了人性,世间凡人有了神性,三性共同构成《西游记》美妙的幻想艺术。而这份幻想艺术是珍贵的、不可多得的,正如钟婴先生在《解读<西游记>》一书中讲的那样,《西游记》的幻想艺术,是一份宝贵的思维财富和丰富的艺术财富。